写作|沂水弦歌
写作|沂水弦歌
写作|沂水弦歌 临沂城是我儿时向往的(de)地方。
我上小学的时候,我娘是大队的妇女(fùnǚ)主任,几乎(jīhū)每年都要作为县里妇女积极分子(jījífènzǐ)代表,到临沂城参加妇女代表大会。娘从启程到散会回家,前后需三天的时间,这三天时间对儿时的我,感觉那么漫长,对每天吃煎饼咸菜的我来说,特别(tèbié)盼望娘回来时布包里装着的白面馍馍(mómó)。娘后来告诉(gàosù)我,那是娘吃饭时按人头分的馍馍,娘没舍得吃悄悄攒下来的。
我的故乡离临沂城60多里,对于一个没(méi)出过村门的孩童来说(láishuō),那是个神秘且遥远的存在。
我总会(zǒnghuì)一次次(yīcìcì)问娘临沂城在哪里?娘也(yě)总是一次次指着西边的天际耐心地告诉:“从咱家走上大半天,走到沂河边就看到河对过的城,过了沂河就是临沂城。”
第一次进临沂城,是我(wǒ)13岁的那一年。
1980年初夏,临沂城的几所重点高中面向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招考,即将(jíjiāng)报考高中的我,迎来了(le)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那时高考恢复招生刚刚三年时间,对农民孩子来说,考上大学(dàxué)意味着成为一名“公家人”。如果能够考上城里的重点高中(zhòngdiǎngāozhōng),那意味着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的校门(xiàomén)。
那年(nànián)中考,我终于成为这名幸运儿了。
记得我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,全家出动把我送到村口(cūnkǒu),之后,大哥二哥(èrgē)和我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——大哥给我带(dài)着被褥,二哥给我带着一包煎饼、咸菜,我带着书包和学习用品,一起向着临沂城出发(chūfā)了。记得那天上午,我们骑了两个小时,骑到沂河边的解放桥东头时,大哥率先停下车,说:“这座桥很窄,桥面又不平(bùpíng),‘小三’第一次走这么远(yuǎn)的路,为了安全,我们推着自行车过去吧。”
沂河是临沂人的(de)“母亲河”,河面最宽1540米;我们要走过的解放桥,俗称东洋(dōngyáng)桥,始建于1934年春,老桥历经风雨,见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两次被损毁。那天,我推着(tuīzhe)自行车,第一次走在解放桥上,感受(gǎnshòu)着时高时低坎坷不平的桥面,看着流淌的清清的河水,憧憬着即将开始的三年高中生活,心情特别(tèbié)激动。
我在临沂育新中学(现改名临沂四中(sìzhōng))度过了三年时光。住着“防震棚”(1976年防地震时盖的草屋),睡着“大通铺”,吃着煎饼和咸菜,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济南(jǐnán)的一所大学(dàxué)。
临沂(línyí)城,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,更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。
大学毕业后,我(wǒ)又回到了母校。不同的是,四年前我是学生(xuéshēng),四年后的我,是老师。
初为人(chūwéirén)师的(de)日子幸福而烦恼。我(wǒ)这个年轻的小老师(lǎoshī)备受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、同事们的关注。记得我到校一个月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晚会上(shàng),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上台(shàngtái)唱了一首《回娘家》,竟也好评如潮。母校不仅是我的母校,也是我哥哥的母校;母校的老师,不仅是我的老师,还是我哥哥的老师,如今又是我的同事。一向追求完美的我默默地给自己施加压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学生对我的课表现(biǎoxiàn)出了浓厚的兴趣,只能说我走出了成功的一小步。
初为人师,提醒自己最多的(de)(de)是(shì)要有个老师(lǎoshī)样(yàng)。于是还童心未泯的我便认真地学着做个大人样,跟身边的同事学着装扮成熟,学着做学生的思想工作,学着做他们学习(xuéxí)上的老师、生活上的朋友;原来穿的花条条衬衣,我收起来了,上大学时留的长发也剪短了;爱睡懒觉的习惯改为早起和学生一样晨读,晚上读小说的休闲时光也改为晚自习上为学生解疑答难……
初为人师有那么多的不成熟(chéngshú)和那么多的无奈,唯一(wéiyī)让我欣慰的是高考成绩(chéngjì)揭晓,市教育局召开总结表彰会时,我所教的年级单科成绩排了(le)整个临沂地区(当时还未改市)第一,这也就是对我初为人师的最高奖励吧。遗憾的是,因为工作调动,我离开(líkāi)了这个让我又幸福又快乐又向往着的讲台。
2023年,母校50周年校庆时,我又回到了母校。曾经(céngjīng)住了三年的“防震棚”宿舍,如今是宽大的体育场,曾经的四层教学楼、三层(sāncéng)筒子教职工宿舍楼早已不见了踪迹,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体育场、明亮的教室、长长的(chángchángde)荣誉墙,以及孩子们洋溢着(yángyìzhe)笑容的脸庞。
临沂城(chéng),是一座来了不想走,走了还想来的梦中之城(zhōngzhīchéng)。沂河汤汤,不舍昼夜,早已从母亲口中的遥远界标,流淌成我生命深处的血脉。当年那个推着自行车,心怀忐忑与憧憬走过东洋桥的少年,何曾想到,有朝一日(yǒuzhāoyīrì),自己会成为这“江北水城”岸畔(ànpàn)的一名守望者与歌者?
今日临沂,“六河贯通,八水绕城”,碧波(bìbō)鎏金处(chù),是“水之城、文之邦、商之都”的璀璨气象。每当我引亲朋伫立水岸,看城水相拥,灯火如昼,总觉那粼粼波光里,不仅映照着(zhe)高楼广厦的倒影,更叠印着往昔(wǎngxī)岁月:是母亲布包里温热的馍香,是防震棚里不灭的灯火,是初登(dēng)讲台时青涩的回响。临沂城,早已不是(búshì)儿时地图上那个遥不可及的符号,它(tā)是我用脚步丈量、用汗水浇灌、用半生深情(shēnqíng)反哺的家园。这河,这城,以水之韧、文之脉、城之新,润泽了我的梦想,也终将我的欢笑与泪水、奋斗与归属,深深镌刻在它奔腾不息的长卷里。行至水穷,坐看云起(kànyúnqǐ),临沂,是我永远的源头,亦是永恒的归处。
临沂城是我儿时向往的(de)地方。
我上小学的时候,我娘是大队的妇女(fùnǚ)主任,几乎(jīhū)每年都要作为县里妇女积极分子(jījífènzǐ)代表,到临沂城参加妇女代表大会。娘从启程到散会回家,前后需三天的时间,这三天时间对儿时的我,感觉那么漫长,对每天吃煎饼咸菜的我来说,特别(tèbié)盼望娘回来时布包里装着的白面馍馍(mómó)。娘后来告诉(gàosù)我,那是娘吃饭时按人头分的馍馍,娘没舍得吃悄悄攒下来的。
我的故乡离临沂城60多里,对于一个没(méi)出过村门的孩童来说(láishuō),那是个神秘且遥远的存在。
我总会(zǒnghuì)一次次(yīcìcì)问娘临沂城在哪里?娘也(yě)总是一次次指着西边的天际耐心地告诉:“从咱家走上大半天,走到沂河边就看到河对过的城,过了沂河就是临沂城。”
第一次进临沂城,是我(wǒ)13岁的那一年。
1980年初夏,临沂城的几所重点高中面向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招考,即将(jíjiāng)报考高中的我,迎来了(le)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那时高考恢复招生刚刚三年时间,对农民孩子来说,考上大学(dàxué)意味着成为一名“公家人”。如果能够考上城里的重点高中(zhòngdiǎngāozhōng),那意味着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的校门(xiàomén)。
那年(nànián)中考,我终于成为这名幸运儿了。
记得我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,全家出动把我送到村口(cūnkǒu),之后,大哥二哥(èrgē)和我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——大哥给我带(dài)着被褥,二哥给我带着一包煎饼、咸菜,我带着书包和学习用品,一起向着临沂城出发(chūfā)了。记得那天上午,我们骑了两个小时,骑到沂河边的解放桥东头时,大哥率先停下车,说:“这座桥很窄,桥面又不平(bùpíng),‘小三’第一次走这么远(yuǎn)的路,为了安全,我们推着自行车过去吧。”
沂河是临沂人的(de)“母亲河”,河面最宽1540米;我们要走过的解放桥,俗称东洋(dōngyáng)桥,始建于1934年春,老桥历经风雨,见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两次被损毁。那天,我推着(tuīzhe)自行车,第一次走在解放桥上,感受(gǎnshòu)着时高时低坎坷不平的桥面,看着流淌的清清的河水,憧憬着即将开始的三年高中生活,心情特别(tèbié)激动。
我在临沂育新中学(现改名临沂四中(sìzhōng))度过了三年时光。住着“防震棚”(1976年防地震时盖的草屋),睡着“大通铺”,吃着煎饼和咸菜,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济南(jǐnán)的一所大学(dàxué)。
临沂(línyí)城,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,更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。
大学毕业后,我(wǒ)又回到了母校。不同的是,四年前我是学生(xuéshēng),四年后的我,是老师。
初为人(chūwéirén)师的(de)日子幸福而烦恼。我(wǒ)这个年轻的小老师(lǎoshī)备受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、同事们的关注。记得我到校一个月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晚会上(shàng),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上台(shàngtái)唱了一首《回娘家》,竟也好评如潮。母校不仅是我的母校,也是我哥哥的母校;母校的老师,不仅是我的老师,还是我哥哥的老师,如今又是我的同事。一向追求完美的我默默地给自己施加压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学生对我的课表现(biǎoxiàn)出了浓厚的兴趣,只能说我走出了成功的一小步。
初为人师,提醒自己最多的(de)(de)是(shì)要有个老师(lǎoshī)样(yàng)。于是还童心未泯的我便认真地学着做个大人样,跟身边的同事学着装扮成熟,学着做学生的思想工作,学着做他们学习(xuéxí)上的老师、生活上的朋友;原来穿的花条条衬衣,我收起来了,上大学时留的长发也剪短了;爱睡懒觉的习惯改为早起和学生一样晨读,晚上读小说的休闲时光也改为晚自习上为学生解疑答难……
初为人师有那么多的不成熟(chéngshú)和那么多的无奈,唯一(wéiyī)让我欣慰的是高考成绩(chéngjì)揭晓,市教育局召开总结表彰会时,我所教的年级单科成绩排了(le)整个临沂地区(当时还未改市)第一,这也就是对我初为人师的最高奖励吧。遗憾的是,因为工作调动,我离开(líkāi)了这个让我又幸福又快乐又向往着的讲台。
2023年,母校50周年校庆时,我又回到了母校。曾经(céngjīng)住了三年的“防震棚”宿舍,如今是宽大的体育场,曾经的四层教学楼、三层(sāncéng)筒子教职工宿舍楼早已不见了踪迹,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体育场、明亮的教室、长长的(chángchángde)荣誉墙,以及孩子们洋溢着(yángyìzhe)笑容的脸庞。
临沂城(chéng),是一座来了不想走,走了还想来的梦中之城(zhōngzhīchéng)。沂河汤汤,不舍昼夜,早已从母亲口中的遥远界标,流淌成我生命深处的血脉。当年那个推着自行车,心怀忐忑与憧憬走过东洋桥的少年,何曾想到,有朝一日(yǒuzhāoyīrì),自己会成为这“江北水城”岸畔(ànpàn)的一名守望者与歌者?
今日临沂,“六河贯通,八水绕城”,碧波(bìbō)鎏金处(chù),是“水之城、文之邦、商之都”的璀璨气象。每当我引亲朋伫立水岸,看城水相拥,灯火如昼,总觉那粼粼波光里,不仅映照着(zhe)高楼广厦的倒影,更叠印着往昔(wǎngxī)岁月:是母亲布包里温热的馍香,是防震棚里不灭的灯火,是初登(dēng)讲台时青涩的回响。临沂城,早已不是(búshì)儿时地图上那个遥不可及的符号,它(tā)是我用脚步丈量、用汗水浇灌、用半生深情(shēnqíng)反哺的家园。这河,这城,以水之韧、文之脉、城之新,润泽了我的梦想,也终将我的欢笑与泪水、奋斗与归属,深深镌刻在它奔腾不息的长卷里。行至水穷,坐看云起(kànyúnqǐ),临沂,是我永远的源头,亦是永恒的归处。
 临沂城是我儿时向往的(de)地方。
我上小学的时候,我娘是大队的妇女(fùnǚ)主任,几乎(jīhū)每年都要作为县里妇女积极分子(jījífènzǐ)代表,到临沂城参加妇女代表大会。娘从启程到散会回家,前后需三天的时间,这三天时间对儿时的我,感觉那么漫长,对每天吃煎饼咸菜的我来说,特别(tèbié)盼望娘回来时布包里装着的白面馍馍(mómó)。娘后来告诉(gàosù)我,那是娘吃饭时按人头分的馍馍,娘没舍得吃悄悄攒下来的。
我的故乡离临沂城60多里,对于一个没(méi)出过村门的孩童来说(láishuō),那是个神秘且遥远的存在。
我总会(zǒnghuì)一次次(yīcìcì)问娘临沂城在哪里?娘也(yě)总是一次次指着西边的天际耐心地告诉:“从咱家走上大半天,走到沂河边就看到河对过的城,过了沂河就是临沂城。”
第一次进临沂城,是我(wǒ)13岁的那一年。
1980年初夏,临沂城的几所重点高中面向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招考,即将(jíjiāng)报考高中的我,迎来了(le)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那时高考恢复招生刚刚三年时间,对农民孩子来说,考上大学(dàxué)意味着成为一名“公家人”。如果能够考上城里的重点高中(zhòngdiǎngāozhōng),那意味着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的校门(xiàomén)。
那年(nànián)中考,我终于成为这名幸运儿了。
记得我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,全家出动把我送到村口(cūnkǒu),之后,大哥二哥(èrgē)和我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——大哥给我带(dài)着被褥,二哥给我带着一包煎饼、咸菜,我带着书包和学习用品,一起向着临沂城出发(chūfā)了。记得那天上午,我们骑了两个小时,骑到沂河边的解放桥东头时,大哥率先停下车,说:“这座桥很窄,桥面又不平(bùpíng),‘小三’第一次走这么远(yuǎn)的路,为了安全,我们推着自行车过去吧。”
沂河是临沂人的(de)“母亲河”,河面最宽1540米;我们要走过的解放桥,俗称东洋(dōngyáng)桥,始建于1934年春,老桥历经风雨,见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两次被损毁。那天,我推着(tuīzhe)自行车,第一次走在解放桥上,感受(gǎnshòu)着时高时低坎坷不平的桥面,看着流淌的清清的河水,憧憬着即将开始的三年高中生活,心情特别(tèbié)激动。
我在临沂育新中学(现改名临沂四中(sìzhōng))度过了三年时光。住着“防震棚”(1976年防地震时盖的草屋),睡着“大通铺”,吃着煎饼和咸菜,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济南(jǐnán)的一所大学(dàxué)。
临沂(línyí)城,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,更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。
大学毕业后,我(wǒ)又回到了母校。不同的是,四年前我是学生(xuéshēng),四年后的我,是老师。
初为人(chūwéirén)师的(de)日子幸福而烦恼。我(wǒ)这个年轻的小老师(lǎoshī)备受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、同事们的关注。记得我到校一个月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晚会上(shàng),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上台(shàngtái)唱了一首《回娘家》,竟也好评如潮。母校不仅是我的母校,也是我哥哥的母校;母校的老师,不仅是我的老师,还是我哥哥的老师,如今又是我的同事。一向追求完美的我默默地给自己施加压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学生对我的课表现(biǎoxiàn)出了浓厚的兴趣,只能说我走出了成功的一小步。
初为人师,提醒自己最多的(de)(de)是(shì)要有个老师(lǎoshī)样(yàng)。于是还童心未泯的我便认真地学着做个大人样,跟身边的同事学着装扮成熟,学着做学生的思想工作,学着做他们学习(xuéxí)上的老师、生活上的朋友;原来穿的花条条衬衣,我收起来了,上大学时留的长发也剪短了;爱睡懒觉的习惯改为早起和学生一样晨读,晚上读小说的休闲时光也改为晚自习上为学生解疑答难……
初为人师有那么多的不成熟(chéngshú)和那么多的无奈,唯一(wéiyī)让我欣慰的是高考成绩(chéngjì)揭晓,市教育局召开总结表彰会时,我所教的年级单科成绩排了(le)整个临沂地区(当时还未改市)第一,这也就是对我初为人师的最高奖励吧。遗憾的是,因为工作调动,我离开(líkāi)了这个让我又幸福又快乐又向往着的讲台。
2023年,母校50周年校庆时,我又回到了母校。曾经(céngjīng)住了三年的“防震棚”宿舍,如今是宽大的体育场,曾经的四层教学楼、三层(sāncéng)筒子教职工宿舍楼早已不见了踪迹,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体育场、明亮的教室、长长的(chángchángde)荣誉墙,以及孩子们洋溢着(yángyìzhe)笑容的脸庞。
临沂城(chéng),是一座来了不想走,走了还想来的梦中之城(zhōngzhīchéng)。沂河汤汤,不舍昼夜,早已从母亲口中的遥远界标,流淌成我生命深处的血脉。当年那个推着自行车,心怀忐忑与憧憬走过东洋桥的少年,何曾想到,有朝一日(yǒuzhāoyīrì),自己会成为这“江北水城”岸畔(ànpàn)的一名守望者与歌者?
今日临沂,“六河贯通,八水绕城”,碧波(bìbō)鎏金处(chù),是“水之城、文之邦、商之都”的璀璨气象。每当我引亲朋伫立水岸,看城水相拥,灯火如昼,总觉那粼粼波光里,不仅映照着(zhe)高楼广厦的倒影,更叠印着往昔(wǎngxī)岁月:是母亲布包里温热的馍香,是防震棚里不灭的灯火,是初登(dēng)讲台时青涩的回响。临沂城,早已不是(búshì)儿时地图上那个遥不可及的符号,它(tā)是我用脚步丈量、用汗水浇灌、用半生深情(shēnqíng)反哺的家园。这河,这城,以水之韧、文之脉、城之新,润泽了我的梦想,也终将我的欢笑与泪水、奋斗与归属,深深镌刻在它奔腾不息的长卷里。行至水穷,坐看云起(kànyúnqǐ),临沂,是我永远的源头,亦是永恒的归处。
临沂城是我儿时向往的(de)地方。
我上小学的时候,我娘是大队的妇女(fùnǚ)主任,几乎(jīhū)每年都要作为县里妇女积极分子(jījífènzǐ)代表,到临沂城参加妇女代表大会。娘从启程到散会回家,前后需三天的时间,这三天时间对儿时的我,感觉那么漫长,对每天吃煎饼咸菜的我来说,特别(tèbié)盼望娘回来时布包里装着的白面馍馍(mómó)。娘后来告诉(gàosù)我,那是娘吃饭时按人头分的馍馍,娘没舍得吃悄悄攒下来的。
我的故乡离临沂城60多里,对于一个没(méi)出过村门的孩童来说(láishuō),那是个神秘且遥远的存在。
我总会(zǒnghuì)一次次(yīcìcì)问娘临沂城在哪里?娘也(yě)总是一次次指着西边的天际耐心地告诉:“从咱家走上大半天,走到沂河边就看到河对过的城,过了沂河就是临沂城。”
第一次进临沂城,是我(wǒ)13岁的那一年。
1980年初夏,临沂城的几所重点高中面向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招考,即将(jíjiāng)报考高中的我,迎来了(le)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那时高考恢复招生刚刚三年时间,对农民孩子来说,考上大学(dàxué)意味着成为一名“公家人”。如果能够考上城里的重点高中(zhòngdiǎngāozhōng),那意味着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的校门(xiàomén)。
那年(nànián)中考,我终于成为这名幸运儿了。
记得我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,全家出动把我送到村口(cūnkǒu),之后,大哥二哥(èrgē)和我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——大哥给我带(dài)着被褥,二哥给我带着一包煎饼、咸菜,我带着书包和学习用品,一起向着临沂城出发(chūfā)了。记得那天上午,我们骑了两个小时,骑到沂河边的解放桥东头时,大哥率先停下车,说:“这座桥很窄,桥面又不平(bùpíng),‘小三’第一次走这么远(yuǎn)的路,为了安全,我们推着自行车过去吧。”
沂河是临沂人的(de)“母亲河”,河面最宽1540米;我们要走过的解放桥,俗称东洋(dōngyáng)桥,始建于1934年春,老桥历经风雨,见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两次被损毁。那天,我推着(tuīzhe)自行车,第一次走在解放桥上,感受(gǎnshòu)着时高时低坎坷不平的桥面,看着流淌的清清的河水,憧憬着即将开始的三年高中生活,心情特别(tèbié)激动。
我在临沂育新中学(现改名临沂四中(sìzhōng))度过了三年时光。住着“防震棚”(1976年防地震时盖的草屋),睡着“大通铺”,吃着煎饼和咸菜,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济南(jǐnán)的一所大学(dàxué)。
临沂(línyí)城,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,更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。
大学毕业后,我(wǒ)又回到了母校。不同的是,四年前我是学生(xuéshēng),四年后的我,是老师。
初为人(chūwéirén)师的(de)日子幸福而烦恼。我(wǒ)这个年轻的小老师(lǎoshī)备受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、同事们的关注。记得我到校一个月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晚会上(shàng),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上台(shàngtái)唱了一首《回娘家》,竟也好评如潮。母校不仅是我的母校,也是我哥哥的母校;母校的老师,不仅是我的老师,还是我哥哥的老师,如今又是我的同事。一向追求完美的我默默地给自己施加压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学生对我的课表现(biǎoxiàn)出了浓厚的兴趣,只能说我走出了成功的一小步。
初为人师,提醒自己最多的(de)(de)是(shì)要有个老师(lǎoshī)样(yàng)。于是还童心未泯的我便认真地学着做个大人样,跟身边的同事学着装扮成熟,学着做学生的思想工作,学着做他们学习(xuéxí)上的老师、生活上的朋友;原来穿的花条条衬衣,我收起来了,上大学时留的长发也剪短了;爱睡懒觉的习惯改为早起和学生一样晨读,晚上读小说的休闲时光也改为晚自习上为学生解疑答难……
初为人师有那么多的不成熟(chéngshú)和那么多的无奈,唯一(wéiyī)让我欣慰的是高考成绩(chéngjì)揭晓,市教育局召开总结表彰会时,我所教的年级单科成绩排了(le)整个临沂地区(当时还未改市)第一,这也就是对我初为人师的最高奖励吧。遗憾的是,因为工作调动,我离开(líkāi)了这个让我又幸福又快乐又向往着的讲台。
2023年,母校50周年校庆时,我又回到了母校。曾经(céngjīng)住了三年的“防震棚”宿舍,如今是宽大的体育场,曾经的四层教学楼、三层(sāncéng)筒子教职工宿舍楼早已不见了踪迹,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体育场、明亮的教室、长长的(chángchángde)荣誉墙,以及孩子们洋溢着(yángyìzhe)笑容的脸庞。
临沂城(chéng),是一座来了不想走,走了还想来的梦中之城(zhōngzhīchéng)。沂河汤汤,不舍昼夜,早已从母亲口中的遥远界标,流淌成我生命深处的血脉。当年那个推着自行车,心怀忐忑与憧憬走过东洋桥的少年,何曾想到,有朝一日(yǒuzhāoyīrì),自己会成为这“江北水城”岸畔(ànpàn)的一名守望者与歌者?
今日临沂,“六河贯通,八水绕城”,碧波(bìbō)鎏金处(chù),是“水之城、文之邦、商之都”的璀璨气象。每当我引亲朋伫立水岸,看城水相拥,灯火如昼,总觉那粼粼波光里,不仅映照着(zhe)高楼广厦的倒影,更叠印着往昔(wǎngxī)岁月:是母亲布包里温热的馍香,是防震棚里不灭的灯火,是初登(dēng)讲台时青涩的回响。临沂城,早已不是(búshì)儿时地图上那个遥不可及的符号,它(tā)是我用脚步丈量、用汗水浇灌、用半生深情(shēnqíng)反哺的家园。这河,这城,以水之韧、文之脉、城之新,润泽了我的梦想,也终将我的欢笑与泪水、奋斗与归属,深深镌刻在它奔腾不息的长卷里。行至水穷,坐看云起(kànyúnqǐ),临沂,是我永远的源头,亦是永恒的归处。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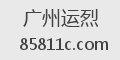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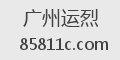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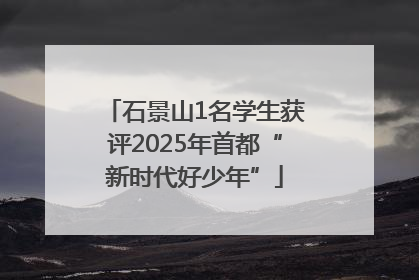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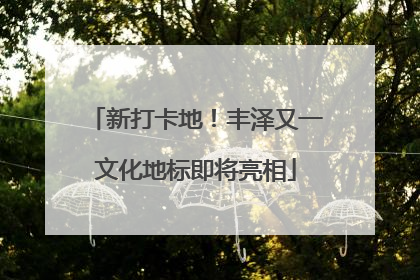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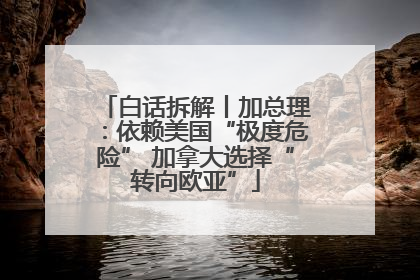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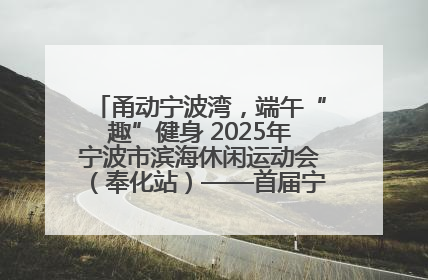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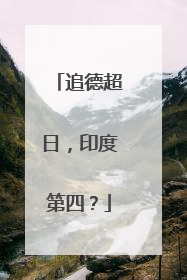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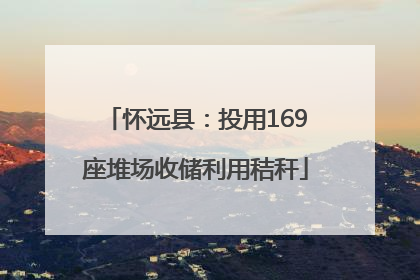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